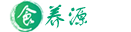从律诗诗体发展角度看,其体式的基本成型是在初唐,时间范围大致从太宗朝到武后朝,这一时期的创作主体是聚集于皇帝身边的文馆学士集团,创作内容以应制诗为主,是适应宫廷和贵族的需要而写,内容是歌功颂德,词句以典雅华丽为尚。因此,从内容上讲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却是律诗形式确立的一个重要时期。
初唐:律诗诗体形式的定型
一、
注重形式的创作环境
自齐梁至初唐,律诗的产生过程一直围绕着宫廷,“永明体”的周颙、沈约、王融、谢脁等人是南齐朝廷的知名文士,“宫体诗”则是基于梁简文帝父子萧纲、萧绎的提倡,在这种提倡中,梁代的宫廷文人徐擒、徐陵、庾肩吾等争相创作,从而使之极盛一时。时至初唐,从事律诗创作的大都是文馆(文学馆,修文馆,弘文馆)学士,这些文馆学士实际相当于皇帝的文学侍从。初唐共有四个这样的学士集团,即太宗朝的文馆学士集团,高宗朝的文馆学士集团,武后朝的珠英学士集团和中宗朝的景龙学士集团。文馆学士的任务一方面是讨论学术文化,倡导礼乐文化,另一方面还要商榷文艺,作诗唱和。
那么初唐时期的文馆学士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创作的呢?简单说,就是游宴赋诗、君臣唱和。据胡震亨《唐音癸签》统计,太宗与高宗朝的宴集赋诗就有近20次,中宗时为唐代之最,自景龙二年七夕至四年四月六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宴集赋诗达37次。宴集的缘由五花八门,有节日、出游、游览宫苑、生日、满月、送朝官、看游戏等。《新唐书》记载了唐中宗时期的游宴情形:“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1]在帝王召集的宴会上赋诗当然要以歌颂为主体,此类应制诗在内容上自是乏善可陈,形式上却要用尽心思、呈奇斗艳,杨慎《升庵诗话》谓“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命题既同,体制复一,其绮绘有余,而微乏韵度”[2]是为的评。应制诗创作的好坏主要在形式上的声韵和技巧。律诗的形式即是在此种风习中确立起来的。而类书及诗格类书的编纂又进一步促成了律诗形式规范的形成。
初唐朝廷热衷于组织文馆学士们进行类书的编纂,这在无形中促成了律诗语词的精致化。类书大量收集古今美文、秀句和丽辞,分类纂辑,目的是为皇室或贵族提供范文和材料,以备写诗作文之用。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四朝,每朝都要聚集学士编纂类书,而且卷帙浩繁。闻一多认为类书直接影响到了唐初诗作的风格:“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3]闻一多批评初唐诗作如类书一般堆砌词藻,从另一个角度讲,文馆学士们在编纂类书的过程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语词经验,其结果就是诗文语言越来越趋于精致化。武后时代,珠英学士徐彦伯的写作“多变易求新,以凤阁为鹓阁,龙门为虬户,金谷为铣溪,玉山为琼岳,竹马为篠骖,月兔为魄兔,进士效之,谓之‘徐涩体’”[4]徐彦伯喜欢求新求变,其表现就是用书面语替换常用语,如用“琼岳”替换“玉山”,唤“月兔”为“魄兔”等,这其实就是受了类书的影响,因为换字易词本就是类书的内容之一。律诗的有些修辞格式也明显来自类书,如将成语典故进行人为的压缩,《初学记》中就把魏武帝曹操作“乌鹊南飞”诗之事简省为了“魏鹊”[5],律诗用典中也常见这种缩略用法。因此,类书的出现无疑更加深了律诗对仗求工整以及语词求典丽的形式特征。
初唐诗坛上还出现了大量用于近体诗学习的诗格类书,包括诗格、诗式等。诗格的编写体例与类书极为相似,一般都是先解释,然后大量示例,与类书“以类相从”的编排法如出一辙。
唐人诗格之作,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重格律,强调诗歌声律的严密性;二是重法式,讲究作诗方法的规范化[6]。如果说齐梁时期关于诗歌格律的论著还是新生事物,只有少数精通音韵的文士写作的话,那么初唐文坛上这类论著已经是普及性的了,从太宗贞观后期到武后长安末年约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大量专以近体诗语言形式为研究对象的论著,知名者如:佚名《文笔式》《诗格》《诗式》,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等,对于形式的重视几乎弥漫于整个社会:“颙、约以降,兢、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空海《文镜秘府论》序) [7]诗格类论著大都集中于近体诗的声韵、病犯、对偶及体式的探讨,其总体特点是在“永明体”的基础上着意于律诗整体结构的完善。
诗格书在初唐的普及是初唐诗坛的一个重要特征,盛唐以后,此类大谈声律属对的诗格书籍就不多见了。从律诗诗体发展的历史过程看,这一现象表明初唐诗坛还处于律诗形式的建设过程中,而正是这些大量专注于诗体形式的研究最终促成了这一新诗体的真正确立。
总体而言,初唐的社会文化环境以注重形式为突出特征,正是在此氛围中,律诗的诗体形式得以在齐梁诗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进而成型。具体表现为:对仗模式的完善;粘对规则的成熟以及形式规则在沈宋创作实践中的实现。
二、
对仗模式的完善与粘对规则的成熟
初唐律诗对仗模式的完善经过了上官仪、元兢、崔融三个阶段[8]。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对偶形式笼统总结为“正对”“反对”“事对”“言对”四种,上官仪则进一步进行了细化,提出“六对”和“八对”的模式,而且还从音义两个方面对对仗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现将“六对”“八对”的模式列举如下[9]:
六对:
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
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
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
四曰双声对,“黄槐”“柳绿”是也。
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
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
八对:
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
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是也。
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是也。
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联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是也。
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
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
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是也。
总体来看,上官仪总结的“六对”和“八对”,其对仗模式常见,也较易模仿创作,与之相比,元兢总结出的对仗模式就带有了深层开掘的意义。元兢也总结出了“六对”:平对、奇对、同对、字对、声对、侧对。他的贡献在于十分注意挖掘对仗的内在对应机制,注重对仗的新奇效果,“奇对”注重内在的对应:如“曾参”对“陈轸”,“参”与“轸”都是二十八宿名;“字对”讲究以字的字别义相对,如“桂楫”对“荷戈”,“桂”与“荷”相对,“荷”在此处是背负的意思,但因为与“桂”同属花草类,所以即以“荷”字的花草之义相对。“声对”是利用字的谐音作对,如“晓路”对“秋霜”,“路”是道路,与“霜”本不成对,但“路”与“露”谐音,所以即可成对。“侧对”是用字的半边相对,如“冯翊”对“龙首”,“冯”字的半边是“马”,可以与“龙”相对[10]。如果说上官仪的“六对”和“八对”还侧重于对仗的一般性总结的话,那么,元兢的“六对”显然深化了对仗的内在对应机制。
元兢之后,崔融又对元兢的“六对”中的“侧对”做了深化,补充了三种:切侧对、双声侧对、叠韵侧对。切侧对如“浮钟霄响彻,飞镜晓光斜”,“浮钟”与“飞镜”相对,一是钟,一是月,本不同理,但粗看文面相对,“钟”与“镜”又同用“金”旁,所以称切侧对;双声侧对如“花明金谷树,叶暎首山薇”,“金谷”与“首山”相对,只是双声相对,但文面不同,所以称双声侧对;叠韵侧对如“自得优游趣,宁知圣政隆”,“优游”与“圣政”相对,都是叠韵,字面之意亦不相对,故称叠韵侧对。崔融的这三种对仗明显是在元兢“侧对”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
律诗的对仗模式在上官仪手中已完成基本面貌,元兢和崔融进行了深化,开掘了对仗的内在对应机制。上官仪的“六对”和“八对”比较拘泥于对仗字面意义的相对,元崔二人的对仗类型则明显呈现出内在对应机制的灵活变化。后世总结标准律诗的对仗,其特征在于:语法结构相同;字不能相同;词性相同;意义相对。对照来看,初唐有关对仗的总结中已完全体现出了这些规则要求。
除对仗模式外,初唐时期还建立了律诗声律模式上的另一重要规则:联间相粘。学界一般认为,这一规则的确立基于元兢“调声三术”中的“换头论”[11]:
换头者,若兢《于蓬州野望》诗曰:“飘飖宕渠城,旷望蜀门隈。水共三巴远,山随八阵开。桥形疑汉接,石势似烟回。欲下他乡泪,猿声几处催。”此篇第一句头两字平,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平;次句头两字又平,次句头两字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又去上入,次句头两字又平。如此轮转,自初以终篇,名为双换头,是最善也。
所谓“换头”,就是要求律诗上联对句与下联出句的头两个字或第二个字在平仄上要一致,即律诗粘对规则中的“粘”。粘对规则中的“对”是早在“永明体”时就已建立了的。“对”针对的是一联之内的平仄对应,但只有“对”,律诗的变化就只是在一联之内。两联以上,平仄模式就会重复,这也是齐梁诗在形式上的最大缺陷。“粘”建立了联与联之间的规则,要求上联对句与下联出句第二字的平仄相同,这样就保证了上下两联不会雷同。有了“粘”,律诗才会真正形成八句的篇制。元兢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他的《诗髓脑》中还有较为明确的将四声二元化为平仄两声的意识,这种思想或许直接影响到了同时代的沈佺期和宋之问。
这样,到初唐,随着对仗模式的细化与粘对规则的确立,律诗体式的完整模式即告完成。
三、
律诗的篇章结构到初唐定型为八句
除声律规则与对仗模式外,律诗的篇章结构也是诗体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律诗的篇章并非一开始就定为八句,要到初唐时,八句才成为一种固定模式。
齐梁时期,人们对律诗形式的探索主要集中于两句,对于篇章的句数没有做限制,于是16句、14句、12句、10句的诗都有。其时联间相粘的规则尚未形成,所以在这些篇章中就往往对句过密,造成同一种平仄模式的多次重复。当时的诗论家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指出了这种弊病,如梁简文帝批评谢灵运的诗有“冗长”的缺点[12](《与湘东王书》),钟嵘在《诗品》中也指出谢灵运、颜延之、谢脁的诗歌有此类毛病:“颜延、谢庄,尤为繁密”[13] ;“(谢灵运)颇以繁芜为累”[14] ,“(谢朓)微伤细密”[15]。自齐梁至南朝后期,八句的诗越来越多,葛兆光以谢灵运、谢朓、庾信三人的新体诗为例,统计有一表,可以很直观地说明这一趋势,现将此表复录于下(格式略有变动)[16]:

从时间顺序上讲,越到南朝后期,随着律诗形式的渐趋定型,八句就越多,从创作主体看,庾信的诗作在南朝诗人中合律程度最高,他的八句诗也作得最多。到初唐,八句才成为律诗的正体。
四、
沈佺期、宋之问的创作实践最终使律诗诗体真正定型
随着律诗形式规则的确立,沈佺期、宋之问的创作实践最终使得律诗诗体真正定型。“沈宋”都是文馆学士,因此,他们的成就依然是基于文馆学士的总体创作氛围,而他们之所以被定为律诗的定体代表,主要在于其律诗的创作技艺在同时代人中最为纯熟。
在沈佺期、宋之问的诗中,完全合乎声律标准的五律已经很多,七律也有合格的。从后人对“沈宋”的评价来看,他们的贡献主要在形式方面:
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17] (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18](《新唐书·文艺中》)
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 [19](《新唐书·文艺上》)
五言至沈宋始可言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20](王世贞《艺苑卮言》)
可见,沈、宋之作能被后世称为“律诗”之祖,主要就在其能“稳顺声势”“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研揣声音”“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很显然,这些评价都集中于诗作的声律篇章形式。
那么,沈、宋之作较之“永明体”“宫体诗”到底有哪些形式上的改进呢?今人大致总结为以下三点[21]。
1.将“平上去入”四声转为了平仄二声,只以二声的交替配合进行创作。这很可能是吸收了元兢声调二元化的思想,并将之付诸创作实践。这种声调二元化的规范不仅使声音的区别变得清晰简洁,创作上也更具可操作性。
2.掌握了联间相粘的规则,从而修正了齐梁诗人“有句无篇”的缺陷,真正写出了符合粘对规则的律诗。
3.作品呈现出了律诗的完整格式。“永明体”对一首诗的句数未作规定,对偶也无明确的位置要求,一韵到底也不那么严格。“沈宋”则严格限于五言八句,且中间两联必须对仗,押平声韵,一韵到底,已是后世眼中完整的律诗格式了。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律诗成于“沈宋”之说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陈铁民认为,不能单纯将律诗定型之功归于“沈宋”,而应归功于初唐的文馆学士集团,“沈宋”只是隶属于其中[22]。邝健行提出,“沈宋”之前,律调已完成,他认为,元兢《诗髓脑》中所说的“换头术”完成了律诗的粘对规则,即表示律调自此完成,时间是在“沈宋”之前的高宗后期,邝健行对初唐五律进行了统计,认为在合律程度上,宋之问的作品粘对不合格的地方比较多,所以律诗成于“沈宋”之说值得商榷[23]。支持“沈宋”之说的学者对以上两种观点均有回应。贾晋华认为,律诗的定型固然与“沈宋”所属的珠英学士集团有密切关系,但之所以将定型之功归之于“沈宋”,一是因为他们的写作实践成功地运用了律诗规则,一是因为公元702年沈佺期主持进士考试时将“诗”纳入了应试内容之一,并规定了声律和修辞准则以及应试诗的字数和句数,同时将其命名为“律诗”。在此期间,宋之问或许给予了协助,或许还在六年后他自己主持的进士试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规定。这就可以解释何以后人多以“沈宋”为律诗定型的代表。杜晓勤指出,元兢虽然发现了“换头术”,却并没有马上被人们接受,对当时诗坛创作的影响也不大,“沈宋”二人的贡献在于不但将律体的诸规则付诸实践,而且通过自己在诗坛的号召力和影响,使得朝野之士纷纷仿效。[24]
综合以上各种探讨及前述律诗体式成型的社会环境,我们认为,比较全面地理解应该是,初唐以来的学士集团与各种类书与诗格类著述为律诗的定型提供了创作环境,奠定了创作基础,“沈宋”则真正在创作实践上将之完成并进一步将这种新诗体推广开来。
综上所述,若自“永明体”算起,则到公元七世纪的“沈宋”,通过声律规则、对仗模式及篇章结构的一步步完善,律诗诗体形式的建立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漫长过程,才终于达到了体制的成熟。
· 参考文献 ·
[1]《新唐书》卷202,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48页。
[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87页。
[3]闻一多:《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0页。
[4]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219页。
[5]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页。
[6]蔡镇楚:《唐人诗格与宋诗话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1994第3期,第20-25页。
[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562页。
[8]罗根泽:“对偶说的历史,盖源于唐初,而成于元兢、崔融。”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02页。罗氏没有明确指出上官仪,他认为上官仪所言“六对”“八对”不是他一人的创造,而是唐初士人的普遍知识,尽管如此,罗根泽在谈及唐初对偶起点时,还是放在上官仪名下谈,因此,我们依然可以认为上官仪是初唐律诗对仗模式完善的第一站。
[9]魏庆之:《诗人玉屑》,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5-166页。
[10]元兢“六对”之例参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99-301页。
[11]乔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8-99页。
[12]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52页。
[13]钟嵘著,陈延傑注:《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4页。
[14]钟嵘著,陈延傑注:《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9页。
[15]钟嵘著,陈延傑注:《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48页。
[16]葛兆光:《汉字的魔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17]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4-15页。
[18]《新唐书》卷202,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51页。
[19]《新唐书》卷20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38页。
[20]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4页。
[21]参见杨仲义、梁葆莉:《汉语诗体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22]陈铁民:《论律诗定型于初唐诸学士》,《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23]邝健行:《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及其相关问题之讨论》(《唐代文学研究》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此外,王梦鸥认为,初唐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元兢的《诗髓脑》及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等诗学著述对诗律的建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沈宋”的作用值得商榷。(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24]杜晓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唐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作者简介
陈 静,山东大学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教授。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古代出版文化;近年来关注女性与出版问题。出版有《唐宋律诗流变研究》《图说中国文化·艺术卷》《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文学评论卷》《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所撰传统文化普及类作品输出版权到韩国。
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未经许可,请勿使用。
本文来自投稿,作者:时遇,不代表食养源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ayuan17.com.cn/yszs/448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