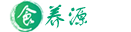将近知天命之年,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虽然仍是平凡之身,从未享受过奇馐珍馔之类的高级美食,可是老百姓口中的普通豆腐,倒是天南海北的各类口味品尝过不少。例如天寒地冻的东北,“咕咕嘟嘟”冒着腾腾热气的白肉酸菜火锅内,饱吸肥厚油脂和酸爽滋味的老豆腐,筋道醇香,每个蜂窝状的气孔都胀满欲罢不能的诱惑;花团锦簇的江浙地带,餐桌上那盆鲫鱼水豆腐,是每个家庭日日必吃的美味佳肴,浓郁乳白的汤汁,白如凝脂,切成四方小丁的水豆腐块,滑溜软嫩,清香适口,仿佛尽收江南水乡灵气,温软舒适,让人忘却一切尘世烦恼;气候湿润的天府之国四川,麻辣劲爆到让人口舌跳动浑身大汗淋漓的“麻婆豆腐”,吃一次不过瘾还想再吃第二次,就像说话嗓门奇大的川中兄弟姐妹,豪气干云,骨子里透着与生俱来睥睨奇险奇绝处境的性情;中原地带的地锅豆腐,千层豆腐,煎炸烹炒均可,口味敦厚纯朴,一如古道热肠的父老乡亲,一如滋养万物生灵的黄土地,厚德载物,生生不息。曹雪芹老爷子说“三千弱水,我只爱一瓢独饮”,我仿佛悟了几百年前先生心迹,芸芸豆腐类别,偏偏对家乡那款独有的热豆腐,耿耿于心,半生牵挂,尽管它做法简陋,口感粗砺。现在想想,在家乡老村,每一个等待买豆腐吃豆腐的黄昏,都是那么诗意隽永,尤其那位卖豆腐的老汉,外貌语言,举手投足,似在眼前,一份感动,依然缱绻心间。推着木架子车,车把上晃荡一盏灯光昏黄的马灯,走村串户卖热豆腐的老汉,七十多岁,衣着朴素,头发花白,满脸皱纹,与我那经年累月在黄土地上默默耕耘的父辈极似,忠厚朴实,毫不起眼,像田间地头一株野草,似沟坎渠边一抔泥土,但他说话豪爽,声音洪亮,嗓门大到犹如千年巨钟撞击之音。夜幕降临,天边最后一抹残霞淡去,倦鸟投林,鸡鸭归圈,连家犬也都安静下来,悠悠晚风吹过高大的杨树枝梢,手掌般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母亲煮好红薯稀饭,蒸好馒头,就等父亲买回热豆腐就馍吃饭。

此时村中十字街口,叔叔、婶婶,上点岁数的哥哥、嫂嫂们,手拿各式各样的碗、盘,陆陆续续聚拢来,父亲也在其间。或蹲或站,一边悠闲地抽着烟,谈笑风生,说古论今,一边耐心等待老汉的到来。“热——豆——腐!”或略微早些,或迟些,这拉长尾音的声调都会不失时机地在村道上空响起,悠长余韵,经清凉晚风勾勒,顿时活色生香。人们嬉笑着聚拢来,老汉停稳车,一面热情而略有歉意地和乡亲们打招呼,一面拿根支棍支住前面车把,以便车子平稳,然后拿出一把短剑样的刀子,一手迅速掀开车中央木托盒内豆腐上盖的洗得雪白的包布,一股腾腾热气夹着清新豆香瞬间扑面而来。老汉问:“您要多少钱的?”“我五毛!”“我八毛!”“我一块!”……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纷纷递钱过去。老汉不慌不忙,竖一刀,横一刀,然后刀一拨,手一托,一小块豆腐稳稳拿起,放进秤盘,秤杆一挑,高高翘起尾巴,喊一声“妥了!”随即放下秤,一手把豆腐托放掌心,一手快速挥刀,切好的豆腐块顺势掉落碗或盘中,切好放下刀,抓住豆腐托盒旁一个白塑料壶的把手掂起,三两下旋开壶盖,壶嘴一倾,一股红色辣椒水混和乳白豆汁,紫黑香椿末的调料液浇在碗或盘内豆腐上,买者遂喜笑颜开端碗或盘走开。称豆腐也有一次不准的时候,老汉就放下秤,再切一块补上,买者就说:“差一点无所谓的。”老汉却正色,大嗓门说:“那咋行!亲是亲,钱财要分真,自己人更不能缺斤短两!”旁边有人接过话头:“这老头,怪不得生意恁好!斤是斤,两是两的!”又有人说:“那是哩!要不然两儿一个闺女咋能都考上大学,当上国家干部呢!”老汉笑起来,还是响亮亮的嗓门:“还不都得感谢大家伙的帮衬。”大伙都笑,纷纷和他开玩笑:“你还卖啥豆腐!三个孩子这个给点,那个要点,你就吃不清喝不净了!”“真是哩,这老头有福不会享!”老汉不笑了,又一脸严肃,声音却低了些:“我好胳膊好腿的,自己挣钱自己花多痛快,人不都得有个念想,精神头才足吗!”众人都说:“这老头,想得真开!”老汉走了,“热——豆——腐”的叫卖声又被晚风吹得飘来荡去,昏黄的马灯光在暮色四合的黑暗中晃晃悠悠……事过经年,无论身在何处,但凡瞥见豆腐身影,那位满面沧桑却坚强乐观的老人,那穿透黑暗晃晃悠悠的马灯光,立即扑进脑海,鲜活生动,如在昨天,大豆清香、辣椒味道与家乡水汽组合的特有味道更强烈霸占味蕾,“人都得有个念想,精神头才足”那句话,如穿透暮色的那盏马灯光,照亮心灵。无独有偶,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和自小一起光屁股长大,小争执不休的新华,以优异成绩被镇重点中学免试录取,从而结束了烂漫的少年时光,开始在热火朝天的中学校园迎接勃发的青春。不曾想,在此又和热豆腐迎面邂逅,并结下难解之缘,深刻体会到那句话的内涵。

我们寄宿在校,从家里带麦子交到学校食堂,以百分之七十的出粉率换成内用粮票。可是,伙食极差,用一句难听的话形容,就不是人吃的。馒头蒸得时好时差,好的时候雪白暄软,差时黑黄黏牙,极难下咽,有时惹得毕业班学生拿起馒头像雨点般砸向伙房,稀饭名副其实地稀,能当镜子照脸,还半生不熟,大锅盐水煮菜,看不到一点油花。实在吃不下去了,我们就用家里给的少得可怜的一点生活费,买一角两角钱的热豆腐吃。校园里有两个拉加子车卖热豆腐的,开饭时进园卖,饭毕离开,据说都和校长沾亲带故。两人也都是老年人。切豆腐的手法相似,豆腐三下两下在手掌里切好放进碗内,浇上一点辣椒汁。也没有油、调味品什么的,就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绝不亚于山珍海味。我们吃得狼吞虎咽,津津有味,有时为了多吃一个馒头,就把馒头掰开来一点一点抹净碗底残余汁液,直到碗干干净净,像用水刷过一样。我们两家家境相似,都极其困难,连一份热豆腐都吃得如此没脾气,不由激发起强烈的斗志,都把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当作追求的梦想,学习格外刻苦。后来因了种种原因,我们没能如愿迈进大学校门,但极富拼搏和开创精神的新华,于2000年挑着担子进了北京,摆地摊卖水果,卖菜,受排挤,受窝囊气,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熬过,终于站稳脚跟,有了长期大量的客户,有了房子有了车。一块平常普通的热豆腐,一勺平淡无奇的辣椒汁,却组合成人间最美的味道,升华出最震撼人心的精神。家乡的热豆腐,我永生最爱。
*作者简介:殷国然,70后,沈丘人,喜爱阅读和写作。文学创作以小说和诗歌为主
本文来自投稿,作者:时遇,不代表食养源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ayuan17.com.cn/ysys/43702.html